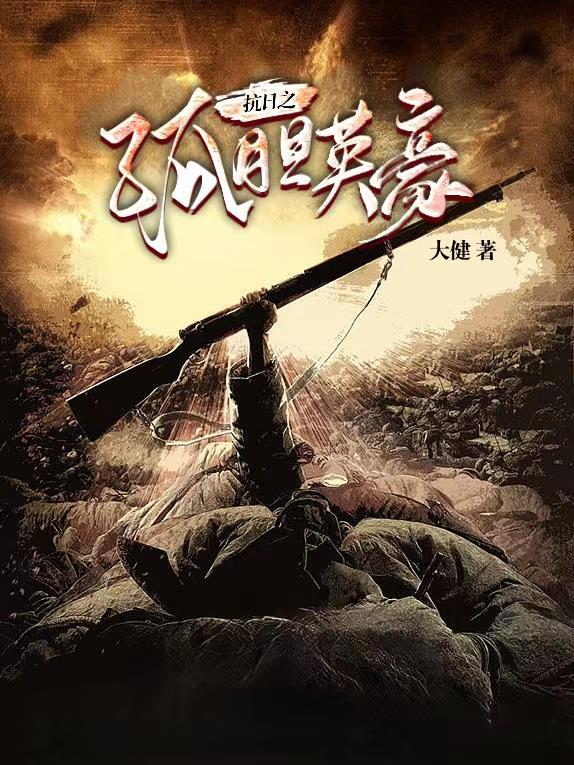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假面自白 > 第三章(第1页)
第三章(第1页)
谁都说人生像个舞台。不过,像我这样从行将结束少年期开始,就一直被人生是个舞台这种意识纠缠住的人,恐怕为数不多。这已经是一种确实的意识,但它非常朴素,同浅薄的经验夹杂在一起,令我心中总有些疑惑:“人们不会像我这样走向人生吧?”但我内心七成相信,任何人都是这样开始自己的人生的。我乐观地相信:只要表演完毕,好歹就会闭幕。我早死的假说与此有关。到了后来,这种乐观主义,或者不如说梦想,遭到了非常严厉的报复。
为慎重起见,我必须补充一句,我在这里想说的不是通常的“自我意识”的问题。仅仅是性欲的问题,而并非其他问题。
本来所谓劣等生的存在是来自先天性的素质,而我为了想跟普通人一样升班,就采取了权宜之计的手段。即考试的时候,我不知其内容,都偷偷地照抄了同学的答案,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交了答卷。有时候,这种比作弊更无智慧、更厚颜无耻的方法会获得表面上的成功。他升班了。以低一年级所掌握的知识为前提上课时,只有他全然不懂。就是听课也全然不明白。他的前途只有两条,一条是走上歧途,另一条是拼命装懂。究竟走哪条路,这是由他的软弱性和勇气的气质来决定,而不是由量来决定的。因为不论走哪条路,都需要等量的勇气和等量的软弱性。而且不论走哪条路,都需要有一种对怠惰的如同诗一般的持久的渴望。
有一回,我加入一伙人的队伍,从学校的围墙外,边走边七嘴八舌地议论某个不在场的伙伴,说他喜欢上了乘坐往返学校的公共汽车上的女售票员。不久,这种背后议论就被一般评论所取代,认为公共汽车女售票员有什么好呢。于是,我有意识地用冰冷的口吻扔下一句话:
“可能是喜欢她的制服呗。穿在她身上很适体,觉得好呗。”
当然,我压根不曾领略过女售票员这种肉感的魅惑。这是类推——纯粹是一种类推——再加上我希望对待事物能拥有像大人那样冷漠的好色之徒的看法,这种与年龄相应的自我炫耀也帮了忙,让我说了这番话。
我所得到的反应有些过度了。这伙人都是品学兼优的稳健派。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真惊人,你真有两下子!”
“要不是有相当经验,说不出这种一针见血的话来呀!”
“实际上,你好像很可怕啊!”
碰上这种天真而令人感动的批评,我觉得太切中要害了。同样的话,也可以用不那么刺耳的朴实的说法,也许这种说法会使人对我留下某种深刻的印象。我反省着,说话应该多斟酌些啊!
十五六岁的少年在操作这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意识时,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为唯有自己比其他少年能够更早地形成坚定的意念,才有可能操作自己的意识。其实不然。我的不安,我的不确定,只不过是比谁都早地要求限制自己的意识。我的意识,只不过是错乱的工具。我的操作,只不过是不确定的胡猜的估量罢了。根据茨威格的定义,“所谓恶魔性的东西,都是天生在所有人的内部,走向自己的外部,驱使人超越自己,走向无限境界的不安定的东西。”而且,它“恰似自然从其过去的混沌中,把某种不应除去的不安定的部分,留在我们的灵魂里”。这种不安定的部分带来了紧迫,且“欲图还原到超人性的超感觉的因素”。在意识具有单纯的解说效用的时候,人就不需要意识,也是合乎道理的。
我本人丝毫也没有从女售票员那里接受其肉体的魅惑,可是却有意识地以纯粹的类推和通常的技巧说了那番话,使伙伴们震惊、羞愧和满脸绯红。而且他们以青春期特有的敏感的联想能力,从我的言谈中隐约地领受到肉感的刺激。目睹眼前的这般情景,我当然涌现出人的要不得的优越感来。然而,我的心并非到此为止。这回轮到我本人受欺骗了。因为优越感发生了偏颇的醒悟。过程是这样的:一部分优越感使我自命不凡,以为自己比别人进步,从而自我陶醉,这陶醉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快醒悟过来。尽管其他部分尚未觉醒,自己却以为所有部分都已醒悟,犯了估计上的错误。所以,“比别人先进”这种自我陶醉,后来被“不,我也和大伙是一样的人啊”这种谦虚感所修正。而由于估计上的错误,又被演绎成“当然在所有点上我和大家是一样的人”这种说法(还没觉醒的部分,使这种演绎成为可能,并支持了它),终于得出“谁都是这样子”的狂妄的结论,意识不过是错乱的工具,在这里起了强有力的作用……就这样,完成了我的自我暗示。这种自我暗示,这种非理性的、愚蠢的、虚伪的,乃至连自己都察觉到明显欺瞒的自我暗示,从这时候起至少占据了我的生活的百分之九十。我想,也许没有什么人比我对附体现象更脆弱了。
读了这些,人们可能明白了吧。其实理由很简单,我之所以能够说出公共汽车女售票员有点肉感的话来,就是因为我对这一点没有觉察到——这确实是很简单的理由,归根结蒂,我对女性的事情没有像其他少年所有的那种先天性的羞耻。
为了避免招来责难,说我只不过是用现在的思考来分析当时的我,现将十六岁时我自己所写的一节抄录如下:
“……陵太郎毫不犹疑地加入了陌生的朋友中。他的举止显得比较快活——也许是佯装让人看的——因为他相信可以把那毫无理由的忧郁和倦怠掩盖起来。迷信作为信仰最良好的因素,把他置在一种白热化的静止形态中。他一边参与无聊的嬉笑和耍闹,一边却不断地在想:‘我现在既不郁闷,也不寂寞。’他将这称为‘忘却了忧愁’。
“自己是幸福的吗?这样也算快活吗?周围的人始终不断地为这样的疑问而感到苦恼。正如疑问这个事实是最实在的东西一样,这是幸福的正当的理想状态。
“然而,陵太郎独自下了定义‘是快活’,并把自己置在确信之中。
“人们的思想,会按这种顺序向他所说的‘确实的快活’发展下去。
“虽说朦胧,却是真实的东西,它被有力地封锁在虚伪的机械里。机械开始强有力地运动了。人们却没有察觉到自己就在‘自我欺骗的房间’里……”
——“机械开始强有力地运动了。……”
机械果真强有力地运动了吗?
少年期的缺点就是,相信只要把恶魔英雄化,恶魔就会心满意足。
不管怎么说,我向人生迈步的时刻逼近了。我登上这个旅途的预备知识,就是许多小说、一册性典、朋友中轮流传阅的淫书、野外演习的每夜里,从朋友那里听来的许多淫猥之谈……首先就是从这里开始。炽烈的好奇心胜过这所有的一切,是我忠实的旅伴。我认为出门的准备也只是“虚伪的机械”,这种决心是最为上乘的。
我仔细研究过许多小说,调查过我这般年龄的人如何感受人生,如何对自己搭话。没有寄宿,没有参加运动俱乐部,再加上我的学校里装腔作势的人很多,一旦过了无意识的“低级游戏”时期,就很少介入下流的问题,况且我又非常腼腆,要把这些事情同每个人的本来面目加以对照,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不得不从一般的原则出发作出这样的推理:像“我这般年龄的男孩子”独自一人时会有什么感受呢?在炽热的好奇心方面,我们都经历过完全相同的青春期。到了这个时期,少年对女性的事似乎都会胡思乱想,都会长粉刺,都会终日觉得昏昏沉沉,都会写些甜美的诗。从这个时期起,他们看到性研究的书籍一味叙述有关自渎的害处,也看到另一些书籍叙述“没有多大害处,放心吧”,也就热衷于自渎了。在这一点上,我和他们也是完全一样的!尽管一样,这种恶习的心理对象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我的自我欺骗对此完全置之不闻不问。
首先,他们似乎从“女”字受到了异常的刺激。只要心上闪现一个女字,他们的脸就会飞起一片红潮。可是,从感觉上说,我对“女”字向来就不曾有过比像看到诸如铅笔、汽车、扫帚之类的字所得到的更多的印象。这种联想能力的欠缺,犹如有关片仓的母亲的情况一样,即使同伙伴谈话,也时常表现出把我的存在置于傻瓜的境地。他们认为我是诗人,也就理解了。然而,我有我的想法,我不希望被人认为是诗人(据说诗人肯定要被女性甩)。为了跟他们的话一致,我人工陶冶了这种联想能力。
我不知道他们同我不仅在内在的感觉方面,而且在外在的无形表现方面也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就是说,他们只要看到女人的裸体照片,就马上引起erectio。唯有我不会这样。而且会使我引起这种反应的对象(它从一开始就是根据性倒错的特质,经过奇妙的严格选择)、爱奥尼亚型的青年裸体像等,却没有任何力量能诱发出他们的erectio。
在第二章里,我之所以有意地一一写了erectiopenis的事,就是因为与此有关。因为我的自我欺骗是由于这点的无知所促成的。任何小说的接吻场面,都省略了有关男性的erectio描写。这是当然的,是不必要写的。就是研究性学的书,也省略了连接吻也能引起的erectio。我推察,唯有肉体交欢之前,或者通过描绘其幻觉,才会产生erectio。我没有任何欲望,但到了这种时候也会突然——简直像是来自天外的灵感——产生erectio。我内心的百分之十却在不断低声嘀咕“不,唯有我不会产生吧”,这就形成我的所有形式的不安,并表现了出来。然而,我犯恶习的时候,心中哪怕一次是否也浮现过女性呢?纵令是试验性的。
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我没有这样做只不过是出于我的怠惰!
归根结蒂,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除了我以外的少年们,每晚都梦见头天窥视的妇女一个个裸体在街头来回走动。不知道少年们梦见了女人的乳房,宛如夜里无数次地从海上漂浮上来的美丽水母,女人们的高贵部分张开湿润的阴唇,数十遍数百遍数千遍没完没了地唱着海魔女之歌……
这是出于怠惰?大概是出于怠惰吧?我疑惑。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于我走向人生的勤奋。总之我的勤奋都花费在这一点怠惰的辩护上,都充作使怠惰照旧发展下去的安全保障。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
相邻推荐:[综漫]论港口和水产公司联姻可行性 大家请我当皇帝 糖心初恋 [综武侠]我自倾城 恶毒女配失势后 攻略任务是养殖致富/靠养殖和美食攻略反派 西城往事 唯一奢望 重生金融之路 渣爹成长计划[快穿] 公主只撩小暗卫 表小姐东宫荣宠录 造反的丈夫也重生了 豪门前夫痛哭流涕求我复婚 我靠漫画风靡世界[穿书] 我在逃生游戏里养娃娃 远古海洋复苏后我成了鲛人 东京人 和前男友同班了 穿成修仙大佬的亲闺女[八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