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网>道德情操论 > 第二章 论各种说明美德之性质的学说(第1页)
第二章 论各种说明美德之性质的学说(第1页)
引言
各种关于美德性质的论述,或者说,各种关于什么心性构成卓越且值得称赞的品德的学说,可以被归纳为三个不同的类别。在某些作者看来,美好的心性或品德并不在于哪一种情感,而在于我们的各种情感全都受到适当的治理和引导;那些情感可能是美好的,但也可能是邪恶的,视它们追求什么目标,以及这追求何等激烈而定。因此,根据这些作者的看法,美德在于情感或行为的合宜。
根据其他某些作者的看法,美德在于头脑精明地追求我们自己的私人利益与幸福,或在于适当地治理和引导那些自爱的、那些仅仅在乎私人目的的情感。因此,根据这些作者的看法,美德在于审慎。
另有一组作者主张,美德在于那些仅以他人的幸福为目的的情感,而不在于那些以我们自己的幸福为目的的情感。因此,根据他们的主张,无私的慈悲心或慈善,是唯一能够为任何行动盖上美德戳记的动机。
很明显,美德的性质,或者必须在我们各种不同的情感全都受到适当的治理和引导时,被笼统地归属于我们全部的情感;或者必须被归属于我们的某一类或某一部分情感。我们的情感主要分成自爱的与慈善的两大类。因此,如果美德的性质不能在我们的情感全都受到适当的治理和引导时,被笼统地归属于我们全部的情感,那么,它就必须被归属于那些以我们自己的私人幸福为直接目的的情感,或归属于那些以他人的幸福为直接目的的情感。因此,如果美德不在于情感的合宜,那么,它必定就在于审慎,或在于慈善。除了这三种情形,几乎不可能想象还会有其他任何关于美德性质的理论。我将在下面努力证明,所有其他看起来似乎和这三种都不相同的理论,怎样在本质上和这三种理论中的某一种或另一种其实是一致的。
第一节论主张美德以合宜为本的学说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芝诺[3]看来,美德在于行为的合宜,或者说,在于引发行为的情感和激起这情感的对象相配。
(1)在柏拉图的理论中[4],心灵被认为是某种宛如一个小国家或小共和国的东西,由三种不同的功能或阶级所构成。
第一种是判断的功能,这种功能不仅决定什么是达成某一目的的适当手段,而且也决定什么是适合追求的目的,以及我们应该赋予每一目的多大的相对价值。柏拉图把这种功能十分恰当地称作理性,并且认为它应当成为统治整个心灵的主要功能。很显然,在所谓理性的名称下,他不仅纳入我们据以判断真伪的那种功能,而且也纳入我们据以判断各种欲望和情感是否合宜的那种功能。
各种不同的热情和欲望,虽然是此一统治阶级自然的子民,却这么时常反叛它们的主人,被他归纳成两个不同的组别或阶级。属于第一组的热情,根源于自傲与愤怒,或根源于被烦琐派学者称为易怒的那一部分心灵,包括野心,憎恨,爱面子,怕丢脸,渴望胜利、优越与复仇。这一组热情被认为或者源自于,在我们的语言中通常会被我们以一种隐喻的方式称之为与生俱来的生气(naturalfire)或元气(spirit)的那一部分心灵运作。属于第二组的热情,根源于对享乐的爱好,或根源于被烦琐派学者称为好色的那一部分心灵,包括身体的所有欲望,对舒适与安全的贪恋,以及对所有满足肉欲之事物的喜好。
理性指示我们遵守的,而且在所有冷静的时刻,我们也曾对自己断言最适合我们遵守的那个处世方针,我们很少会中断遵守,除非是受到前述那两组不同的热情中的某一组或另一组的唆使,亦即,除非是受到难以驾驭的野心与憎恨的唆使,或受到眼前的舒适与享乐纠缠不休的恳求。但是,虽然这两组热情是这么容易误导我们,它们仍然被认为是人性中必要的成分:第一组热情的存在,是为了防卫我们免于伤害,为了主张我们在这世上的地位与尊严,为了使我们志向高尚正直,以及为了使我们推崇那些同样志向高尚正直的人;而第二组热情的存在,则是为了提供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和生活必需品。
审慎的精髓在于理性的坚强、敏锐与圆熟。根据柏拉图的看法,审慎的美德在于,根据一般常识和科学理念,对哪些是适合被追求的目的,以及哪些是适合被用来达成那些目的的手段,有一正确与清晰的认识。
当第一组热情,或属于易怒的那一部分心灵的热情,具有这一种程度的坚强与稳固,使它们能够在理性的指挥下,藐视所有可能遇到的危险,一心追求高尚光荣的目的时,这就构成刚毅与宽宏大度的美德。根据这派学说,这一组热情的性质比另一组热情更为慷慨与高尚。它们在许多场合被认为是理性的辅助,帮助理性制止和约束那些比较低级与下流的肉欲。这派学说指出,当贪恋享乐唆使我们做出我们不赞许的事情时,我们时常生自己的气,我们时常成为自己憎恨与愤怒的对象;我们的天性中易怒,就是以这种方式被招来协助理性的那一部分对抗好色的那一部分。
当我们天性中所有那三种不同的部分彼此完全和谐一致时,当不管是易怒的,或是好色的热情,都绝对不会寻求任何不是理性所赞许的目标,而且理性也绝对不会下令执行任何不是那两种热情自动愿意执行的事情时,心灵的此一幸运的平静安详,此一完全圆满的调和一致,构成了那种在他们的语言中以一个被我们译为节制(temperance)的字眼表达的美德;那个字眼或许可以被更适当地译为心平气和(goodtemper)或心灵的沉着与中庸(sobrietyandmoderationofmind)。
最后一个也是四个基本美德中最伟大的那个美德,正义或公平。根据此一学说,当心灵的那三种功能都各自固守其本分,绝不企图侵犯其他任何功能的职责时,当理性指挥而热情顺从时,当每一种热情都各自执行其本分的职责,各自顺畅地、欣然地,并且使用和它所追求的价值相称的那个程度的力气与精神,努力对适当的对象发挥它的功能时,于是构成了柏拉图追随从前某些毕达哥拉斯派学者的说法,称之为正义或公平(Justice)的那种圆满的美德或完全合宜的品行。在此必须注意的是,希腊语中表示正义或公平的那个字眼有好几个不同的意义,而由于所有其他语言中,与那个字眼相当的字眼,就我所知,也都同样有好几个不同的意义,因此,那些不同的意义之间一定有某种自然的近似关系。就某个意义来说,我们算是对我们的邻人做了正义的事,如果我们绝不做任何直接伤害他的行为,亦即绝不直接伤害他的身体,或他的财产,或他的名誉。这就是我在上面论述的那种正义,这种正义的遵守可以被强制要求,违反这种正义会遭到惩罚。[5]就另外一个意义来说,我们不算是对我们的邻人做了正义的事,除非我们在心里头对他怀有的那些爱恋、尊敬与钦佩,是他的品行、他的处境以及他和我们的关系,理当使之适合我们感觉到的全部,并且除非我们在行动上充分表达我们的这些感觉。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对一个于我们有功的人算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没有尽力帮助他,没有尽力把他摆在公正的旁观者乐于看到他在的那个位置上,虽然我们没在任何方面伤害他。那个字眼的第一个意义,和亚里士多德以及烦琐派学者所谓的交换性正义(commutativejustice)相符,也和格劳秀斯[6]所谓的justitiaexpletrix一致,在于绝不侵犯别人的东西,并且自动地做那些反正我们也可以被正正当当地强制去做的事情。那个字眼的第二个意义,和某些学者所谓的分配性正义(distributivejustice)[7]相符,也和格劳秀斯所谓的justitiaattributrix一致,在于适当的慈善,在于适当地使用我们自己的东西,在于把它用在,就我们的处境来说,最适合使用它的那些慈善或慷慨的目的上。就这个意义来说,正义包含一切有助于社会和乐的美德。希腊语的正义或公平有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涵义比前述两个更加广泛,虽然和前述第二个非常近似;而这个意义,就我所知,也是所有语言中表示正义或公平的那个字眼都有的意义。在最后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被认为对某一特定对象不公平,如果我们看起来没有以公正的旁观者认为它似乎应当得到的那个程度的尊重去重视它,或者我们看起来没有以公正的旁观者认为它本质上似乎有能力唤起的那个程度的热情去追求它的话。于是,我们会被认为对某一首诗或某一幅画不尽公平,如果我们对它们的赞美不够充分的话,我们也会被认为对它们公平过了头,如果我们对它们的赞美太过分的话。同样的,我们会被认为对我们自己不尽公平,如果我们看起来没充分注意到任何于我们自己有利的目标。就最后这个意义来说,所谓正义或公平,意思和言行举止正确圆满的合宜完全相同,因此,包含在它里头的,不仅有交换性正义与分配性正义这两种暗示,而且还有其他每一种美德,譬如,审慎、刚毅、节制等等的暗示。柏拉图显然是按最后这个意义在理解他所谓的正义,因此,照他的意思,正义里头包含每一种至为圆满的美德。
以上所述就是柏拉图就美德的性质,或者说,就适合受到称赞与认可的那种心性的性质,所提出的说明。照他的意思,美德在于这样的一种心灵状态,其中每一个功能都固守它自己的本分,绝不侵犯其他任何功能的范围,并且以它本来应有的那个程度的力气与精神严谨地执行专属于它的职责。他的说明,显然在每一方面,都和我们在前面对行为的合宜性所做的说明相符。
(2)美德,根据亚里士多德[8]的看法,在于依据正确的理性,力行中庸的习惯。照他的意思,每一种特定的美德都宛如位于两种相反的恶癖之间的正中央似的,这两种恶癖中的某一种,错在过分为某一种事物所感动,而另一种则是错在太少为同一种事物所感动。譬如,刚毅或勇敢的美德位在怯懦与冒昧鲁莽这两种相反的恶癖的正中间,这两种恶癖中的前一种,错在过分为可怕的事物所感动,而后一种则是错在太少为可怕的事物所感动。又譬如,节俭的美德位在贪婪与浪费这两种相反的恶癖的正中间,这两种恶癖中的前一种,错在对私利事物的注意超过适当的程度,而另一种则是错在对私利事物的注意低于适当的程度。同样的,宽宏大度的美德也位在傲慢自大的过分与优柔胆怯的不足的正中间,这两种恶癖中的前一种,错在对我们自己的价值与尊严感觉过于强烈,而另一种则是错在对我们自己的价值与尊严感觉太过微弱。用不着说,这个关于美德的说明,和前面我们对行为合宜与否的说明,简直是完全相符的。[9]
没错,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与其说在于那些中庸或正确的情感,不如说在于适度或中庸的习性。要了解这一点,读者须注意,美德可以被视为某一行为的性质,或某个人的性质。当被视为某一行为的性质时,美德,甚至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是在于引发行为的那个情感的适度中庸,不论行为人是否惯常有这中庸的情感倾向。当被视为某个人的性质时,美德是在于这适度中庸的习惯,在于这适度中庸的情感已经变成习惯性的与常见的心灵倾向。譬如,由于一时的慷慨奋发而做出来的行为,无疑是一次慷慨的行为,但是,做出这行为的人却未必是一个慷慨的人,因为这也许是他唯一曾经做过的一次慷慨的行为。引发这行为的动机与心性倾向可能是颇为合理适当的。但是,由于此一适当的心性倾向似乎是一时心血来潮的结果,而不是性格中什么恒久不变的因素促成的,所以它不会给行为人带来什么了不起的荣耀。当我们称某一性格为慷慨的或慈悲的性格时,我们的意思是,那些名称中的每一个所表达的那种感情倾向,是行为人平时习惯的倾向。但是,任何单一次的行为,要证明行为人平常有什么习惯,是没有什么用的。如果单有一次行为便足以在行为人身上盖上什么美德的性格戳记,那么,最卑鄙的人也有资格主张自己具备一切美德,因为绝不会有什么人未曾在某些场合做过审慎、公平、节制或刚毅的行为。因此,单一次行为,不论多么值得赞赏,绝不会给行为人带来什么掌声,不过,单一次邪恶的行为,如果是由一个平常循规蹈矩的人犯下的,便会大大降低,有时候甚至完全摧毁我们对他的美德的评价。单一次邪恶的行为便可充分证明,他的习惯不够完美,证明他其实不像我们根据他平常的行为倾向或许很可能认为的那样完全可以信赖。
此外,当亚里士多德主张美德在于实际的行为习惯时,他很可能想要反对柏拉图的学说,后者似乎认为,只要对什么事适合做或什么事当避免,有正确的感觉和适当的判断,便足以构成最圆满的美德。根据柏拉图的看法,美德也许可被视为一门知识,因为他认为,没有人会在一清二楚地知道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之后,却不根据此一对错的知识行动。他认为,热情或许会使我们做出一些和可疑且不确定的意见相反的行为,但绝不会使我们做出任何和明显确定的判断相左的行为。与他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的说服力量不足以撼动根深蒂固的习惯,并且高尚的德性也不是源自知识,而是源自实际的行动。
(3)根据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10]的看法,每一个事物都被自然女神托付给它自己照顾,并且都被自然女神赋予自爱的原理,以便它不仅会努力维持它自己的存在,而且也会努力把它的天赋中所有不同的部分保持在这些能够达到的那个最好且最完美的状态。
人的自爱,拥抱(如果我可以这么说)他的身体和这身体的各个部分,以及他的心灵和这心灵的各种功能与力量,并且希望他的身心全都保持在最好且最完美的状态。因此,凡是有助于保持这个存在状态的,都会被自然女神为他指出来,告诉他那是适合他选择的事物;而凡是倾向摧毁这个存在状态的,也都会被自然女神为他指出来,告诉他那是适合他拒绝的事物。譬如,身体的健康、力气、敏捷与舒适,以及身外各种能够增进方便这些状况的事物,包括财富、权势、荣誉,以及和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人对我们的尊敬与重视,自然会被指出是我们适合选择的事物,而且拥有它们强过没有它们。另一方面,身体的疾病、虚弱、笨拙与疼痛,以及身外各种倾向造成或带来任何不利这些状况的事物,包括贫穷、缺乏权威,以及和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人对我们的轻蔑,也同样会被指出是我们适合避免的事物。那两类相反的事物中,各自有一些事物似乎比其他同一类事物更为可取或更应避免。譬如,在第一类事物中,健康看起来显然比力气更为可取,而力气则比敏捷更为可取;名誉比权势更为可取,权势比财富更为可取。又譬如,在第二类事物中,疾病比身体笨拙更应被避免,不名誉比贫穷更应被避免,而贫穷则比丧失权势更应被避免。美德或行为的合宜,就在于所有这些不同的事物与情况的取舍,完全按照它们被自然女神做成比较是或比较不是我们适合选择或拒绝的标的而定;就在于总是从摆在我们眼前的好几个适合我们选择的标的中,选择那最该被选择的,如果我们不能得到它们全部的话;同时也在于总是从摆在我们眼前的好几个合适我们拒绝的标的中,选择那最不该被避免的,如果我们无法完全避免它们的话。当我们以这样正确精密的识别能力决定取舍,当我们根据每一件事物在这个自然的事物尺度中所占的地位,恰如其分地给予它应得的注意时,我们的行为便可保持圆满正直,而根据斯多葛学派的观点,美德的本质就在于这行为上的圆满正直。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始终如一的生活,顺从自然的生活,以及顺从自然女神或造物主为我们的行为所规定的那些法则与方向的生活。
到此为止,斯多葛学派关于合宜与美德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以及古代的逍遥派学者(thePeripatetics)的理念,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在那些被自然女神推荐给我们视为合适选择的标的中,主要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国家、人类,乃至宇宙万物普遍的繁荣。但是,自然女神也教我们懂得,正如两个人的繁荣比单一个人的繁荣较为可取,所以,多数人的繁荣,或全体的繁荣,一定比什么都更为可取许多。教我们懂得,我们只不过是那一个人,因此,每当我们的繁荣和整体或多数人的繁荣不能两全时,我们的繁荣便应该,甚至在我们能够自由选择时,让位给各种比它较为可取得这么多的繁荣。由于所有发生在这世界的事情,都是在一个贤明、有力与善良的神的眷顾监督下发生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相信,凡是发生的,都有助于全世界的繁荣与圆满。因此,如果我们自己陷入贫穷、生病或其他任何灾难中,我们应该首先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在正义以及我们对别人的责任容许的范围内,把我们自己从这种不愉快的情况中拯救出来。但是,如果在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之后,发现这是不可能办到的,那我们就应该安心满意地认为,宇宙的秩序与圆满需要我们在这个时候继续处在这种情况下。而且由于整体的繁荣,甚至对我们来说,也显得比像我们自己这样微不足道的部分繁荣较为可取,所以,我们的处境,不管好坏,应该从那一刻起成为我们所喜欢的对象,如果我们决心保持我们的天性完美所由构成的那种情感与行为上的完全合宜与正直的话。没错,一旦有任何拯救我们自己的机会出现,拥抱那机会就变成是我们的责任。宇宙的秩序显然不再需要我们继续待在这个处境,因为这世界的伟大主宰,透过如此清楚地指出我们应该遵循的道路,已经明白地要求我们离开那个处境。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的亲属、我们的朋友或我们的国家所处的逆境。如果我们无须违背任何更加神圣的责任,便能够防止或结束他们的不幸,那么,这么做无疑便是我们的责任。行为的合宜,朱比特(Jupiter)[11]为了引导我们的行为而交给我们的那条规则,显然要求我们这么做。但是,如果我们完全没有能力防止或结束他们的不幸,那么,这时候我们便应该认为,他们所遭遇的不幸,是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中最幸运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放心相信,那个不幸最有助于整体的繁荣与秩序,而后者正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是贤明与公正的人)应该最希望实现的目标。那不幸,视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终极利益,因为整体的繁荣应该不仅是我们希望实现的主要目标,更是我们希望实现的唯一目标。爱比克泰德[12]说:“在什么意义上,某些事情据说是符合我们的天性的,而其他一些事情则据说是违反我们的天性的?这是从我们自认为和其他一切东西独立分离的意义来说的。譬如,在这个意义上,始终保持干净,可以说,是符合‘脚’的天性的。但是,如果你认为它是一只脚,而不是某种和身体的其他部分独立分离的东西,那么,它就一定有义务有时候踩入泥土中,有时候踏在荆棘上,有时候甚至为了整个身体的缘故而被割掉;如果它拒绝这些义务,它就不再是一只脚。我们对我们自己也应该作如是观。你是什么?是个人。如果你自认为是某个分离独立的东西,那么,符合你的天性的,就是长寿、富有与健康。但是,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人,是某个整体中的一部分,那么,为了那个整体的缘故,你有义务有时候生病,有时候面对航海的不方便,有时候生活困苦;而最后,也许,在你的天年来到之前死去。然则为什么你要抱怨?难不成你不知道,由于你的抱怨,就像‘脚’不再是一只脚,所以,你也不再是一个人?”
智者绝不抱怨天意安排的命运,当他遭遇不顺时,不会认为这世界是混乱的。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某个整体,独立分离于自然界的其他每一部分之外,靠它自己,也为它自己而存在。他会以伟大的人类守护神,同时也是这世界的守护神(在他想象)会用来看待他的那种眼光,看待他自己。他会体谅并且赞许,如果我可以这么说,那位神明的感觉,并且自认为是某一无限广大的体系中的一个渺小的微分子或微粒子,必须而且也应该依照整个体系怎样才得便利,就受到怎样的处置。他对那个管理人间一切事情的智慧深具信心,因此,凡是临到他头上的命运,不论好坏,他都满怀喜悦地接受,完全相信,如果他知道所有存在于宇宙各部分之间的种种联系与依存关系的话,那命运正是他自己希望得到的命运。如果那命运是生,他会心甘情愿地活下去;如果那命运是死,由于自然女神一定不再需要他存在这世上,他也会欣然前往他被指定的那个地方。某位大儒派的哲学家说,我接受,不论我可能临到什么命运,我都以同等喜悦和满足的心情接受。他的学说在这一点上和斯多葛学派完全一致。富裕或贫穷,快乐或痛苦,健康或生病,全都一样:而我也不希望众神在任何方面改变我的命运。如果在他们的宽大慈悲已经赐予我的一切之外,我还可以向他们请求什么,那就是请他们事先告诉我,他们乐于怎样处置我,以便我可以自动把我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借此证明我由衷拥抱他们的安排。爱比克泰德说,如果我将扬帆出海,我会选最好的船和最好的舵手,而且我也会等待我的处境与责任所允许的最好的天气。审慎与合宜,众神为了引导我的行为而交给我的这两条守则,要求我这么做,但是,它们没有别的要求。尽管如此,如果刮起了那种不论是什么船只的强度或舵手的技巧都不可能抵抗的暴风,我也不会劳神去担心会有什么后果。一切我必须做的,都已经做了。引导我的行为的众神绝不会命令我,要觉得可怜,要焦虑不安,要垂头丧气或感到害怕。我们是否要溺死在海中,或在某个港口安全上岸,是朱比特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完全把这件事留给他决定,我绝不会中断心中的平静去考虑他可能会怎样决定这件事,而会以同样无所谓与泰然的心情接受任何来临的结果。
斯多葛学派的智者,由于对统治宇宙的那个仁慈的智慧抱着这么完全的信心,而且对那个智慧认为合适建立的任何秩序也抱着这么完全顺从的态度,所以,对他来说很自然,所有人生的际遇必定大多无所谓好坏。他的幸福全在于,第一,沉思伟大的宇宙体系的幸福与圆满,沉思那个由众神与人类,由一切有理性有感觉的生命组成的伟大共和国的良好的统治秩序;第二,善尽他的责任,在这个大共和国的日常事务中,适当地扮演他的角色,不论那个智慧分派给他的角色是多么的渺小。他的种种努力是否合宜,对他来说,或许关系重大。它们的成功或失败,对他却不会有任何影响,不会激起任何热烈的喜悦或悲伤,也不会激起任何热烈的愿望或反感。如果他喜好某些事情甚于其他事情,如果某些情境是他选择的对象,而其他情境是他拒绝的对象,那也不是因为前者本身在任何方面比后者更好,或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所谓幸运的情境中会比在所谓不幸的情境中享有更完整的幸福,而是因为行为的合宜,因为众神为了引导他的行为而交给他的这一条守则,要求他必须这样取舍。所有他的心意全被吸纳贯注在两种主要的心意中,他全神贯注在执行他自己的责任,以及希望一切有理性有感觉的生命得到最大可能的幸福。关于后面这个心意的满足,他百分之百安心仰赖伟大的宇宙主宰的智慧与力量。他唯一挂念的是怎样满足前面那个心意,不是挂念会有什么结果,而是挂念他自己的各种努力是否合宜。不论结果是什么,他都相信会有一个优于他的力量与智慧把它用来增进他自己也最希望增进的那个伟大的目的。
这个取舍合宜的原则,虽然最初是被那些受取舍的事物给我们指出来的,也是为了那些事物的缘故而被指出来的,并且可以说,是被那些受取舍的事物推荐和介绍给我们认识的。然而,当我们一旦变得彻底熟悉了这个原则,我们在这种行为中看到的秩序、优雅与美丽,以及我们从这种行为中所感觉到的幸福,对我们来说,必然会显得比实际取得所有不同的适合我们选择的事物,或实际避免所有那些适合我们拒绝的事物,更有价值。人生的幸福与光荣,来自于遵守这个合宜的原则;人生的不幸与耻辱,则来自于忽略这个原则。
但是,对于一个智者来说,对于一个已将他的各种热情完全驯服在他的天性中的统治性原则之下的人来说,要做到正确遵守这个合宜的原则,在所有场合都是同样容易的。如果他处在顺境中,他会感谢朱比特让他处在这么容易把握的情境中,处在这种没有什么诱惑让他做错事的情境中。如果他处在逆境中,他也同样会感谢这个人生场景的导演,为他安排了一个很强劲的比赛对手,虽然和他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不过,赢过他的胜利将会更为光荣,而且这胜利也同样是必然会实现的。处在那种并非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而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困境,如果我们在其中的行为完全合宜,哪会有什么羞耻可言?因此,绝不可能有什么不幸,反而会有最大的幸福与好处。一个勇敢的人,当他面对并非由于他自己的鲁莽所致,而是他的命运使他卷入的那些危险时,反而会欢喜雀跃。那些危险让他有机会运用这么一种英勇无畏的精神,它的发挥,经由意识到自己合宜出众与应受钦佩,会产生意气昂扬的喜悦。一个熟练所有他的运动技巧的人,不会厌恶和最强劲的对手较量他的力气与敏捷。同样的,一个能够克制自己的情感的人,不会害怕所有宇宙的主宰认为可能适合把他摆进去的环境。那位神明的宽大慈悲已使他具备足以超越每一种环境的美德。如果这环境是享乐,他有节制的美德去节制它;如果这环境是痛苦,他有坚定的美德去忍受它;如果这环境是危险或死亡,他有宽宏与刚毅的美德去藐视它。任何人生的变故,绝不可能使他惊惶失措,或使他不知道如何保持,在他的理解中,同时构成他的光荣与他的幸福的那种情感与行为上的合宜性。
斯多葛学派显然把人生看作是一种大有技巧的游戏比赛,然而,其中掺杂机遇的成分,或掺杂某种被世俗理解为机遇的成分。在这种游戏中,赌注通常是微不足道的,游戏的乐趣全来自于玩得好,玩得公平和玩得很有技巧。一个优秀的玩家,尽管用尽了所有他的技巧,然而,由于机遇的影响,如果碰巧输了比赛,他的失败也应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而不应该是一件值得真正感到悲伤的事情。他未曾有什么错误的比赛动作,他未曾做出任何他应该觉得羞耻的事情,他彻底享受了比赛的全部乐趣。相反,一个差劲的玩家,尽管他连连犯错,然而,由于机遇的影响,如果碰巧赢了比赛,他的成功也不可能给他带来什么满足。想起他曾经犯下的任何过错,就觉得羞愧与懊丧。甚至在游戏比赛当中,他也享受不到游戏能够提供的任何乐趣。由于不知道游戏的规则,畏惧、疑惑与犹豫,是他在做每一步游戏动作之前几乎都会有的不愉快的感觉;而当他做完了他的动作后,发现那是严重的错误而感觉到的羞愧与悔恨,通常会填满他整个不愉快的感觉。人的生命,加上所有可能伴随它的种种好处,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解,应该被视为只不过是区区两分钱的赌注;这赌注太过琐碎,不值得任何焦急不安的关切。我们唯一要担心挂念的,应该不是赌注的输赢,而是什么是适当的玩法。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幸福寄托在赢得赌注上面,那么,我们的幸福就得倚靠一些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因素。因此,我们必然会为我们自己招来永久的恐惧与不安,并且往往会为我们自己招来种种难以忍受和令人懊丧的失望。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幸福寄托在玩得好,玩得公平和玩得很有技巧上面,简单地说,就是把它寄托在我们自己的行为的合宜性上面,那么,透过适当的训练、教育与注意,我们的幸福便可能完全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我们的幸福将是百分之百的安全无虞,并且不受命运的影响。我们的行为的结果,如果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那么,它也就同样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绝不会为它感到任何的恐惧或忧虑,当然也就不会蒙受任何难以忍受的,或任何真正的失望。
他们说,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情况,人的生命本身以及各种可能伴随生命而来的好处或坏处,可能是我们应当选择或应当拒绝的对象。如果,在我们实际的处境中,符合人性的情况多于违反人性的情况;如果适合我们选择的情况多于适合我们拒绝的情况,那么,生命在这种场合大致上是适合我们选择的对象,而且行为的合宜性也要求我们保持我们的生命。相反,如果在我们实际的处境中,违反人性的情况多于符合人性的情况,而且没有任何可能改善的希望;如果适合我们拒绝的情况多于适合我们选择的情况,那么,对一个智者来说,生命在这种场合就变成是适合拒绝的对象。因此,他不仅可以自由地弃绝生命而去,而且行为的合宜性,众神为了引导他的行为而交给他的这条规则,也要求他这么做。爱比克泰德说:“我被命令不许住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我就不在那里住。我被命令不许住在雅典,我就不在那里住。我被命令不许住在罗马,我就不在那里住。我被命令必须住在狭小且多岩石的盖尔若(Gyarae)岛上,我就去那里住。但是,盖尔若岛上的房子烟雾弥漫。如果这烟雾不是太大,我会忍受它,待在那里。如果这烟雾实在太大,我会走进一间没有任何暴君能够把我从那里赶走的房子。我会随时记得(这间烟雾弥漫的房子的)大门是敞开的,以便当我高兴时我可以走出去,并且归隐到那间殷勤好客并且永远对全世界敞开的房子,因为除了对我最下层的衣裳之外,除了对我这一身臭皮囊之外,没有任何活着的人有任何力量能够对我怎么样。”斯多葛学派说,如果你的处境整个看起来是不愉快的,如果你的房子,对你而言,烟雾太过弥漫,那你务必往屋外走出去。但是,走出去时,不要鸣不平,不要发牢骚,不要抱怨。要平静地、满足地、开心地走出去,要以感谢回向众神,感谢他们,由于他们无限宽大的慈悲,打开了安全与平静的死亡港口,随时准备接纳我们离开那风狂雨暴的人生大海;感谢他们准备了这个神圣的,这个不可侵犯的,这个伟大的避难所,始终敞开着,始终进得去,完全远离人世间的狂暴与不公平,并且大到足以容纳所有那些愿意,以及所有那些不愿意归隐到它那里的人。这个避难所让每一个人完全没有借口抱怨,或甚至幻想,除了他自己的愚蠢和软弱可能会让他蒙受的那种不幸之外,人生还会有其他什么不幸。在流传至今的少数几篇此派学说的断简残篇中,斯多葛学派的学者们有时候以一种快活,甚至流于轻浮的语气,谈论放弃生命的议题。这种语气,如果我们只考虑那些片段的话,或许会使我们相信他们认为,只要我们想,不管这想法是多么的荒唐与任性,我们便可以因为稍微觉得怄气或不愉快而合宜地放弃生命。爱比克泰德说:“当你和某个这样的人一起吃晚餐时,你抱怨他喋喋不休地诉说他在米西亚[13]打战的冗长故事给你听。他说:‘既然我的朋友已经告诉你,我怎样在如此这般的一个地方占了上风,我就来告诉你,我怎样在如此这般的另一个地方遭到围困。’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想为他的冗长故事感到心烦,那就不要接受他的晚餐。如果你接受了他的晚餐,那你就没有一丁点儿立场抱怨听他说那些冗长的故事。你所谓人生的那些不幸也是一样。绝不可抱怨任何你有能力主动避开的事情。”虽然这说法显得有点轻松甚至轻浮,然而,不同于放弃生命的选项,或继续活下去,在斯多葛学派看来,才是最值得我们慎重考虑的选项。我们绝不该抛弃生命,除非起初赐予我们生命的那个主宰力量清楚地要求我们这么做。但我们将认为我们自己被要求这么做,而这不仅在命定的且不可避免的人生大限时。当那个主宰力量的眷顾安排,使我们今生的处境,整个看起来,变成是适合我们拒绝,而不是适合我们选择的对象时,他为了引导我们的行为而交给我们的那一条伟大的守则,在这个时候,要求我们放弃生命。在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可以说听到了那个神圣的主宰所发出的庄严仁慈的声音,清楚地要求我们这么做。
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斯多葛学派认为,抛弃生命可能是一个智者的责任,虽然他可以过得非常幸福;而相反,继续活下去也可能是一个弱者的责任,虽然他必然过得很不幸福。如果,在智者的处境,自然适合他拒绝的情况多于自然适合他选择的情况,整个处境变成是适合他拒绝的对象,这时,众神为了引导他的行为而交给他的守则,就会要求他尽快在情况方便时抛弃他的生命。然而,他是完全幸福的,甚至在他或许认为应当继续活下去的时候。他不是把他的幸福寄托在获得他所选择的事物上,或寄托在避免他所拒绝的事物上,而是寄托在他的取舍始终严正合宜,寄托在他的种种努力合宜恰当,而不是寄托在他的种种努力获得成功。相反,如果在弱者的处境下,自然适合他选择的情况多于自然合适他拒绝的情况;他的整个处境变成是适合他选择的对象,而继续活下去则是他的责任。然而,由于他不知道怎样利用那些情况,他其实是不幸的。纵令他手上的那一副牌是这么的好,可是他却不知道怎样出那一副牌,因此,不可能享受什么真正的满足,不管是在游戏过程中,或在游戏结束时,不论这游戏碰巧有什么结果。[14]
自愿死亡在某些场合的合宜性,虽然在古代各哲学门派中,也许是最为斯多葛学派所坚持的,然而,其实却是各门各派共同的一个教条,甚至温和慵懒的伊壁鸠鲁学派[15]也有同样的说法。在古代各主要哲学门派的奠基宗师还活着的那个时代,在伯罗奔尼撒战争[16]和战后许多年中,希腊各个共和国,在内,几乎始终处在最激烈的党派斗争纷乱中;在外,则卷入最为血腥凶暴的战争中,每一个共和国在战争中所追求的,不仅是霸权或统治权,而是彻底灭绝所有它的敌人,或者,比较不那么残忍的,也要使他们沦为所有阶级中那个最下贱的阶级,要使他们沦为家奴阶级,要在市场上把他们,不分男女老少,全都像牲畜那样,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而那些国家大部分又是小国,这使得它们每一个并非很不可能正好陷入那种它自己经常作孽使一些邻国陷入的,或至少企图使它们陷入的不幸中。在这样混乱无序的状态中,最没有瑕疵的清白,加上最高贵的身份地位和最伟大的公职服务,也不能保证任何人,即使他待在国内和他自己的亲人与同胞在一起,不会有朝一日由于某一对他怀有敌意与愤怒的党派得势而被判处最残忍与最不名誉的惩罚。如果他在战争中成为俘虏,或者他所属的那个城邦被征服了,他也许会遭遇到更大的伤害与侮辱。但是,每一个人自然,或者毋宁说必然,会使他的想象力熟悉种种他预知他的处境可能常常会使他遭遇到的危难。一个水手不可能不会常常想到暴风雨和船难,想到沉没在大海中,以及想到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和行动。同样的,一个古希腊时代的爱国者或英雄,也不可能不会使他的想象熟悉所有各种他知道他的处境必定常常,或者毋宁说经常,会使他遭遇到的灾难。正如一个美洲的野蛮人会准备他的死亡之歌,并且考虑在他落入敌人的手中,当着所有旁观者的侮辱与嘲笑,被敌人以最受折磨的方式处死时,他该怎样行动那样,一个古希腊时代的爱国者或英雄也不可能避免常常动用他的脑筋,考虑在他被放逐时、被俘虏时、被降为奴隶时、被酷刑折磨时,或被送上绞刑台时,他应该忍受些什么,以及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各门各派的哲学家们全都很恰当地主张,美德,亦即审慎、公平、坚定与节制的行为,不仅是最可能的,而且也是最确实可靠的,通向幸福甚至是今生幸福的道路。然而,这种品行却不可能始终会使坚持这种品行的人免于,有时候甚至还可能为他招来各种难免会在那样纷乱的国家状态中发生的不幸。因此,他们努力证明,幸福或者完全,或者至少大部分和命运无关。斯多葛学派说,幸福完全和命运无关;而柏拉图学派和逍遥学派则说,幸福大部分和命运无关。审慎、公平、坚定与节制的行为,首先是最可能保证每一种事业成功的行为;第二,即使它没获得成功,然而,这时心灵也并非毫无慰藉。有美德的人仍然可以享受他自己的内心所给予的完全赞赏;仍然可以感觉到,不管外面的事情是多么的不顺,内心里的一切都是平静、安详与调和的。他通常也可以安慰他自己,相信他拥有每一个贤明与公正的旁观者的爱与尊敬,相信后者一定会一方面钦佩他的行为合宜,一方面痛惜他的运气不佳。
同时,那些哲学家还努力证明,人生可能遭遇到的一些最大的不幸,比通常想象的还更容易忍受。他们尽力指出任何人仍然可以享受到的各种慰藉,即使陷入贫穷,即使被放逐,即使遭到群众不公平的喧嚣辱骂,即使在目盲、在耳聋、在年老垂死的情况下辛苦过活。他们还指出种种在他受到痛苦甚至酷刑折磨时,在他生病时,在他为失去子女或为亲友死亡等等不幸悲伤时,可能有助于保持他的情操坚定的理由。古代哲学家就这些主题所写的那几篇流传至今的断简残篇,也许是最有教育意义的,同时也是最有趣的古代遗物之一。他们的那些学说的精神与气节,和现代某些学说沮丧、悲哀和哭泣的语气,形成令人叹为观止的强烈对比。
虽然古代那些哲学家这样努力提示每一个能够——套一句弥尔顿[17]的说法——以像三层钢那样顽强的耐性,使坚定的心胸获得武装的理由,但是,他们同时尤其卖力说服他们的门徒相信,死亡本身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不幸;不论在什么时候,如果他们的处境变得太过难堪,以致他们坚定的心胸不再能够负荷时,补救的办法是唾手可得的,人生的大门是敞开的,他们可以随时放心地走出去,只要他们高兴。他们说,如果除了眼前这个,没有其他任何世界存在,那死亡便不可能是不幸的;如果有另外一个世界,众神必定也存在那个世界,在他们的保护下,一个公正的人用不着担心遭遇到任何不幸。总而言之,那些哲学家,如果我可以这么说,准备了一首死亡之歌,以便古希腊时代的那些爱国者和英雄们可以在适当的场合吟唱,而在所有不同的门派当中,斯多葛学派所准备的那一首死亡之歌,显然是最为激昂的,我想这一定是众所公认的。[18]
然而,在希腊人当中,自戕一向似乎决非很普遍的现象。除了克里欧孟尼斯[19],我目前想不起有什么非常著名的希腊爱国者或英雄以他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亚里斯托孟尼斯[20]的死亡,和亚杰克斯[21]的死亡,同样是发生在有确实的历史纪录以前很久的事。西米斯托克利斯[22]之死,虽然发生在信史期间,不过,常见的有关他怎么死的说法,看起来和最浪漫的神话故事没有两样。普鲁塔克[23]对其生平有所记述的所有希腊英雄当中,克里欧孟尼斯似乎是唯一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的人。西拉麦尼斯、苏格拉底和佛西翁[24],这三人显然并不缺乏勇气,容许他们自己被捕入狱,并且甘心忍受同胞们的不公正所判处的那种死刑。勇敢的尤孟尼斯容许他自己被反叛他的士兵递交给他的敌人安迪哥奴斯,然后被活活饿死,完全没有企图自戕。[25]英勇的菲罗波门[26]容许他自己成为梅西尼亚人的俘虏,被关进地牢,并且据说是被秘密毒死的。没错,有好几个希腊哲学家据说是自戕身亡的,但是,那些关于他们生平的记述是这么的愚蠢怪诞,以致有关他们的故事多半不可信。斯多葛学派的奠基者芝诺的死,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说,他在享受了98年最为完美的健康生活后,有一天在走出他的学校时碰巧跌倒,虽然没受到什么损伤,除了一根手指被折断或脱臼,他却很生气地以手击打地面,并且,根据尤里披蒂斯所写的《奈奥比》(Niobe)[27]的叙述,说“我就来了,为什么你要叫我呢?”然后立即回家上吊自戕。一般人大概会认为,在那么大把年纪,他应当更有耐性才是。另一说,他在同一年纪时,因遭遇到类似的意外,之后自己绝食饿死。第三说,他在72岁时寿终正寝。在三种说法中,这显然是最为可信的,而且也有某一当代人的权威支持,这个人绝对有机会知道他的生平事迹,这个人就是柏西乌斯(Persaeus),他原本是奴隶,后来成为芝诺的朋友与门徒。第一种说法出自泰尔的阿波罗尼乌斯[28],他和奥古斯都·恺撒[29]是同一时代的人,大约活跃在芝诺身后两百年至三百年间。我不知道谁是第二种说法的作者。本人是一位斯多葛派哲学家的阿波罗尼乌斯可能认为,对一个谈论这么多自愿死亡的哲学门派的创始人来说,以自己的双手自愿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件光荣的事。文人们,虽然在他们死后,往往比那些和他们同一时代的伟大君主或政治家们受到更多人谈论,但他们生前通常是这么的默默无闻,这么的微不足道,以致他们的生平事迹很少被当代的历史家记录下来。后代的历史家们,为了满足大众的好奇心,而且由于没有任何确实可信的文件可以支持或反驳他们的故事,似乎往往就根据自己的想象捏造他们的故事,并且几乎总是掺杂大量不可思议的成分。在我们目前讨论的这个例子里,不可思议的故事,虽然没有任何权威支持,似乎向来比有可能是事实而且也有最好的权威支持的故事更流行。迪奥基尼斯·莱尔迪乌斯[30]明显偏好阿波罗尼乌斯所写的故事。鲁西安[31]和莱克坦蒂乌斯[32]两人显然也相信芝诺活了一大把岁数后死于非命的故事。
自愿死亡的风气在自傲的罗马人当中流行的程度,似乎远胜过它曾在活泼、灵敏与随和的希腊人当中流行过的程度。甚至就罗马人来说,这风气在罗马共和国早期或所谓美德盛行的时期,似乎也还没有确立。普遍流传的瑞古鲁斯[33]之死的故事,虽然很可能是一则神话。但是,如果当时的人认为,甘心忍受迦太基人据说曾施加在他身上的那些拷打折磨,会给那位英雄带来什么不名誉的话,该则神话就绝不会被捏造出来。在罗马共和国的后期,这种甘心忍受敌人折磨的行为,据我的理解,会招来一些不名誉。在罗马共和国沦亡前的各次内战中,所有斗争的党派中,都有许多地位显赫的人士,选择宁愿亲手了结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落入他们的敌人手中。小加图[34]的死法,被西塞罗(Cicero)赞扬,被恺撒(JuliusCaesar)谴责,成为也许是这世界曾经见过的两位最著名的辩护者之间一场非常严肃的论战的主题,并且赋予这种死法一种历经好几代后似乎仍然未见褪色的光彩。西塞罗的雄辩胜过恺撒的口才。赞扬的这一方大大胜过谴责的那一方,而后来好几代爱好自由的人士也把小加图视为罗马共和派中最值得尊敬的烈士。德利兹枢机主教[35]指出,一个党派的领袖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他持续保有同伙们的信任,他就绝不可能做错什么事。这一则箴言所含的真理,他这位大人,在好几个场合曾有机会亲身体验。小加图,除了有他的其他那些美德之外,似乎还是杯中物的一位了不起的伴侣。他的敌人们指控他老是醉醺醺的,但是,塞涅卡[36]说,凡是根据此一恶癖而反对小加图的人都将发现,要证明酩酊大醉是一项美德,比要证明小加图可能沉迷于任何恶癖,来得更为容易得多。
在罗马帝国时期,这种死法似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非常流行。在普里尼[37]的书信史中,我们发现一则记载说,有好几个人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然而,他们所以这么做,似乎是出于虚荣与卖弄的心理,而不是出于任何在冷静与明智的斯多葛派学者眼中可以算是适当或必要的理由。甚至追随时髦很少落于人后的一些上流社会的仕女们,似乎也往往毫无来由地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并且,像孟加拉国的仕女们那样,在某些场合,陪伴她们的丈夫下葬。这种风气的流行无疑导致许多原本不会发生的死亡。然而,这种风气,也许是虚荣与鲁莽的人性成分发挥的极端,因此,它所可能造成的一切祸害,不论在什么时候,大概都不会很大。
自戕的原则,或者说,那个教我们在某些场合把那种激烈的行为视为赞许与喝彩的适当对象的原则,似乎完全是哲学家凭空思辨琢磨出来的产物。自然女神,在她身心健全的时候,似乎从未鼓舞我们自戕。没错,确实有一种忧郁症(人性,除了其他种种悲惨的状态外,很不幸地,也很容易患这种病),似乎附带有一股抑制不住的自我毁灭的欲望。这种心理疾病,屡见不鲜地把那些不幸为这种病所苦的人,逼向这个致命的极端,尽管这些人的外在环境常常是极其顺利的,有时候甚至尽管他们还有最诚真和最深入内心的宗教信仰。不幸以这样悲惨的方式死去的那些人,不是该受谴责而是该受怜悯的对象。当他们已超越所有人间惩罚的范围时,企图惩罚他们,不仅荒谬,而且这种企图的不公平性也不亚于它的荒谬性。人间的惩罚只可能落在那些比他们后死的朋友和亲属身上,而那些人总是完全无辜的,并且对他们来说,单是以这种不名誉的方式失去他们的朋友,便已经是一件非常严重不幸的事故了。自然女神,在她身心健全时,鼓舞我们在所有场合避免苦恼;鼓舞我们在许多场合保卫我们自己免于苦恼,虽然在那保卫的过程中,我们须冒着灭亡的危险,或甚至必死无疑。但是,当我们既无能力保卫我们自己免于苦恼,也还没有在那保卫的过程中灭亡时,所有自然的原则,所有对想象中的那个公正的旁观者是否赞许的顾虑,或所有对我们心中的那个人的道德褒贬的顾虑,似乎都不会要求我们须以摧毁我们自己来逃避苦恼。只在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懦弱,意识到我们自己无力以适当的男子汉气概和坚毅去忍受不幸,才可能逼使我们采取这样决绝的解脱。我不记得曾经读过或听过有哪一个美洲的野蛮人,在他即将被某个敌对的部族俘虏时,自戕身亡,以免被俘后在敌人的侮辱与嘲弄中被拷打致死。他把他的光荣寄托在以男子汉的气概去忍受那些拷打折磨,以及寄托在以十倍的轻蔑和嘲笑去回敬敌人的那些侮辱。
然而,这种轻蔑生死的态度,以及同时彻底顺从天意的安排,或者说,完全甘心接受人世间的兴替流变可能带来的每一件事故,却可以被视为整个斯多葛道德哲学架构赖以建立的两条最根本的教义。独立自主、勇敢奋发,但常常是严厉冷酷的爱比克泰德,可被视为前述第一条教义的伟大提倡者;而温和、优雅与仁慈的安东尼纳斯[38],则可视为前述第二条教义的伟大提倡者。
那位被义巴弗利蒂图斯解放的奴隶,在他年轻时,遭到一位残忍的主人的傲慢虐待,在他较为成熟时,被性喜猜忌与反复无常的(罗马皇帝)德米雄逐出罗马与雅典,而不得不住在尼科波利斯,并且随时可能被同一位暴君驱逐流放到盖尔若岛,或也许被处死,只能够以在心中培养对人生轻蔑至极的态度来保持他内心的平静。他最为兴高采烈,从而他的雄辩也最为激昂的时候,莫过于当他诉说人生的一切享乐和人生的一切痛苦皆属空无的时候。[39]
那位秉性善良的皇帝[40],身为整个文明世界绝对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无疑没有任何独特的理由抱怨他自己的命运,然而,他却乐于表达他对日常的事态发展所感到的满足,乐于指出,甚至在粗俗的观察者不容易看出有什么赏心悦目之处的那些日常的琐事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惊叹的美丽。他指出,甚至在年老时,也和年轻时一样,有一种合宜性,甚至是动人的优雅,老年人的衰弱老朽和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一样符合自然。而且,死亡是年老的一个适当的结束,正如青年之于幼年,或成年之于青年那样。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说,正如我们常常说,医生指示某某人去骑马,或洗冷水澡,或赤脚走路那样,我们也应该说,自然女神,这位伟大的宇宙主宰与医生,指示某某人罹患某种疾病,或截断部分手足,或失去一个小孩。听从普通医生的指示,病人吞下了许多苦涩的药剂,接受了许多次痛苦的手术。然而,由于抱着结果可能是健康的希望,尽管这希望非常地不确定,他仍然高兴地顺从所有医生的指示。同样的,病人也可以期望大自然的医生所给的那些最严厉的指示,将有助于他自己的健康,有助于他自己最终的繁荣与幸福,并且他可以完全放心相信,那些指示,对宇宙的健康,对宇宙的繁荣与幸福,对朱比特的伟大计划的推行与促进,不仅有帮助而且更是不可免的必要。如果它们不是这么有帮助,也这么有必要的话,宇宙就绝不会产生它们,无所不知的造物主和宇宙的主宰绝不会容许它们发生。由于宇宙所有同时共存的部分,甚至是其中最微小的部分,全都严密地彼此扣合在一起,并且全都有助于构成一个庞大无比且相互连贯的体系,所以,所有一个接着一个相继发生的事件,甚至是那些表面上最微不足道的事件,全是那一条过去不知道从何开始,将来也不会有结束的伟大因果链当中的成分,而且还是必要的成分,而所有那些事件,由于它们全都必然起因于那个根本的整体安排与设计,所以,不仅对整体的繁荣来说,而且也对整体的延续与保全来说,它们全都是根本上必要的。不论是谁,如果他没诚心诚意地拥抱临到他身上的一切,如果他为临到他身上的事情感到难过,如果他但愿那事情没有临到他身上,那他就是希望,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阻碍宇宙的运动,破坏那条伟大的因果环环相扣的链条,尽管唯有透过这条因果链的开展,整个宇宙体系才得以延续与保全,因此,他等于是希望,为了他自己渺小的便利,使整部世界机器陷入混乱乃至解体。他在另一个地方说:“喔,世界,凡是适合于你的,都适合于我。凡是对你是合于时宜的,对我来说,就不会太早或太晚。你的时令产生的,全都是我的果实。一切全出于你,一切全属于你,一切全为了你。某人说,喔,心爱的希克洛普斯城[41]。难道你不会说,喔,心爱的神之城?”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
相邻推荐:白鲸 教书匠 人猿泰山 春 笑林广记 儒林外史 往事与随想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暗箱 故事新编 天幕红尘 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 天空的另一半 小学问:解决你的7种人生焦虑 丑陋的中国人 时光知味 草:最怀念的某年 随园食单 瓦尔登湖 四世同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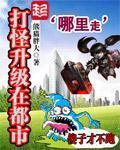
![盗版万人迷[快穿]](/img/1318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