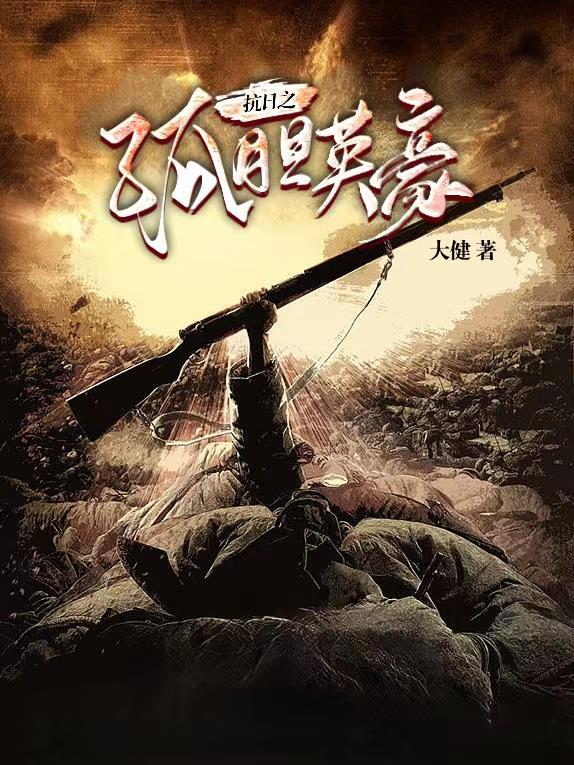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道德情操论 > 第三章 论各种关于赞许之原理的学说(第1页)
第三章 论各种关于赞许之原理的学说(第1页)
引言
在关于美德之性质的研究之后,下一个重要的道德哲学问题是关于赞许之原理,关于究竟是心灵的什么能力或机能,促使我们喜欢或憎恶某些品行,促使我们喜欢某一行为格调而不喜欢另一行为格调,促使我们称其一是对的而称另一是错的,促使我们认为其一是赞许、推崇与奖赏的对象,而另一则是责备、非难与惩罚的对象。
关于道德赞许的原理,历来有三种不同的学说。根据某些学者的观点,我们之所以赞许或非难我们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行为,纯粹是基于自爱,或者说,纯粹是鉴于那些行为对我们自己的幸福有益或有害;根据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理性,即我们用来辨别真假的那一种能力,也同样使我们能够辨别各种行为与情感的适当与否;还有一些学者的观点是,这种适当与否的辨别,完全是直接感觉的结果,完全来自于我们看到某些行为或情感时直接感到满足或憎恶。因此,历来被认为是赞许之原理的,有自爱、理性与感觉等三种不同的源头。
在开始说明这三种不同的学说之前,我必须指出,这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虽然在理论上极为重要,但在实务上却一点儿也不重要。那些探讨美德之性质的研究,必然会对我们在许多特定场合的是非对错观念产生影响。但是,那些探讨赞许之原理的研究,却不会有这种效果。探讨那些不同的念头或感觉来自于我们心中的什么机关或能力,纯然只是一种哲学上的好奇。
第一节论主张赞许之原理本于自爱的学说
那些从自爱的观点解释赞许之原理的学者,论述的方式并非完全相同,而且所有他们的那些不同的理论都含有许多不清不楚与不正确的地方。根据霍布斯先生[66]以及他的许多追随者[67]的观点,人之所以被迫托庇于社会,并非因为他对于他自己的同类有什么自然的爱恋,而是因为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他就不可能生活得很轻松或生活得很安全。因此,对他来说,社会的存在是有必要的,并且凡是有助于社会屹立不摇与幸福安宁的,他都认为间接有助于自己的利益;而相反的,凡是可能扰乱或摧毁社会的,他都认为多少会伤害到自己。美德是人类社会的主要支柱,而恶行则是人类社会的主要乱源。因此,对每个人来说,美德是可喜的,而恶行则是可憎的,因为前者让他预见到那个对他的生活舒适与安全是这么有必要的社会倾向繁荣兴旺,而后者则让他预见到那个社会倾向混乱毁灭。
美德有助于增进,而恶行倾向扰乱社会秩序,当我们冷静地、超然地考虑此一事实的时候,它会给美德增添一层非常美丽的光彩,同时也会给恶行涂上一张非常丑陋的面孔,这一点,正如我在前面某个场合指出的[68],是无可置疑的。人类社会,当我们从某一抽象超然的观点冥思默想它的时候,似乎就像是一部庞大无比的机器,它那有规律的与协调的转动产生无数可喜的效果。正如就其他任何高尚美丽的人造机器而言,凡是有助于使该机器运转更为平滑顺畅的事物,都会因这种效果而显得美丽;相反,凡是倾向妨碍它运转的事物,则会因那个缘故而讨人厌。所以,美德,好比是保持社会齿轮清洁光滑的亮光粉剂,必然叫人喜欢;而恶行则好比是污秽的铁锈,使社会齿轮彼此尖锐抵触与刺耳摩擦,必然叫人讨厌。因此,这个关于道德赞许与非难的学说,就它把赞许或非难溯源自对社会秩序的关心而论,和我在前面某个场合解释过的那个赋予效用以美丽的原理[69]并无二致;而它所拥有的一切近似真理的表相,也正是得自于那个原理。当那些作者描述文明教养的群居生活,相对于未开化的独居生活所享有的那些数不尽的好处时,当他们详细论述美德与良好的言行规矩对于维持前一种生活是多么的有必要,并且证明败坏伦常与不服从法律的行为盛行将怎样毋庸置疑地倾向使后一种生活重返人间时,他们为读者打开的那些新颖与宏伟的视野令他陶醉着迷:他清楚地在美德当中看到一种新的美丽,并且在恶行当中看到一种新的丑陋,这些美丽与丑陋是他以往从未注意到的,他通常是如此陶醉于他的这个新发现,以至于很少花时间去回想,此一政治学的见解,由于是他在以往的生活中从未想过的,绝不可能是他所以向来一直习惯于认为美德应予赞许而恶行应予谴责的根本理由。
另外,当那些作者从自爱推论我们所以关切社会的安宁与幸福,以及我们为了社会的缘故而尊敬美德时,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当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赞美小加图的美德,并且厌恶卡特林纳的恶行时[70],我们的这些情感是受到我们顾及前者可能带给我们什么好处而后者则可能给我们造成什么损害的影响。根据那些哲学家的观点,我们之所以尊敬有美德的人,而谴责败德乱纪的人,并非因为我们认为社会的繁荣或混乱,在那久远的年代与国家,对我们自己今日的幸福或不幸有什么影响。他们从未认为,我们的情感会因为我们推想那两种人实际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利益或损害而受到影响。他们只是认为,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久远的年代与国家,我们的情感将会因为我们推想那两种人可能给我们带来某些利益或损害而受到影响;或者说,如果我们在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遇上了同种性格的人,我们的情感也将会因为我们推想那两种人可能给我们带来某些利益或损害而受到影响。总而言之,那些作者一直在摸索探求的,但一直未能清楚表明的概念,就是我们对于那些因为这两种相反的性格而受益或受害的人心中的感激或怨恨,所感到的那种间接的同情:当他们说,我们的赞美或愤慨所以被唤起,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起我们曾经获得了什么利益或蒙受了什么损害,而是因为我们顾及或想到,如果我们在社会上和那两种人共事,我们很可能会获得某些利益或蒙受某些损害时,他们依稀指向的,就是那种间接的同情。
然而,同情,不论在哪种意义上,都不能被看成是一种自私的性情。没错,也许有人会认为,当我同情你的悲伤或你的愤怒时,我的情感是基于自爱,因为这样的情感源自我使我自己深切领悟你的处境,源自我设想我自己处在你的位置,并且由此怀想我在类似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虽然同情可以很恰当地被认为是源自我和主要当事人的处境有一虚拟的转换,然而,这个虚拟的处境转换却不应被认为是发生在我还是我自己的那个身份与角色上,而应被认为发生在我换成是我所同情的那个人的身份与角色上。当我因为你失去了独子而对你表示哀悼时,为了和你同感悲伤,我心里边想的,不是我,一个具有如此这般的角色与身份的人,如果有一个儿子,而且如果那个儿子不幸死了,我会尝到什么痛苦;而是如果我真的是你,如果我不仅和你交换处境,而且也换成是你那样的身份与角色,我会尝到什么痛苦。因此,我的悲伤完全是因为你的缘故,一点儿也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缘故。因此,它一点儿也不自私。我的同情,甚至不是源自我想到了任何曾经临到我自己的头上,或与我在自己本来的身份与角色上有关的事情,而是完全专注在与你有关的事情上,这样的情感怎能被当成是一种自私的热情?一个男人可以同情一个分娩中的女人,和她同感痛苦,虽然他不可能想象他自己会在他本来的身份与角色上蒙受她的那种痛苦。整个企图从自爱推演出一切道德情感,而且向来是这么的出名,不过,就我所知,却从未被说明得很清楚完整的人性理论,在我看来,似乎是源自于没搞清楚同情的概念。
第二节论主张赞许之原理本于理性的学说
众所周知,霍布斯先生认为,人类原始的状态是一种战争的状态;而且在公民政府建立之前,人类之间不可能有安全或和平的社会。因此,据他所言,要保全社会,就必须拥护公民政府,而摧毁公民政府就等于是终结社会。但是,公民政府的存在有赖大家服从最高的民政长官,一旦他失去了他的权威,整个政府便完蛋了。因此,正如自保的理由教人们赞美任何有助于增进社会安宁的行为,并且谴责任何可能伤害社会的行为那样,如果人们的想法与言行一致的话,同样的道理也该教人们在所有场合赞美服从民政长官,并且谴责所有不服从与造反的行为。什么是值得赞美的与应予谴责的,和什么叫做服从与不服从,应该是同一回事。因此,民政长官所制定的法律,应该被视为判断是非对错以及公正与否的唯一根本标准。
霍布斯先生公开表明的意图,就是要透过传播这些理念,使人们的良心直接服从公民政府的权威而不是服从教会的权威,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事例告诉他,教会的骚乱与野心是社会秩序的主要乱源。神学家们因此特别讨厌他的学说,于是免不了极其尖酸刻薄地对他发泄他们的愤怒。所有纯正的道德学家也同样讨厌他的学说,因为该学说认为是非对错之间没有自然的区别,认为是非对错是无常的,是可变的,是完全取决于民政长官恣意独断的意志的。因此,此一学说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受到各式各样的武器攻击,受到冷静的理智以及狂怒的痛骂攻击。
想要驳倒这个如此叫人讨厌的学说,就必须证明,在所有法律或明文的建制之前,人的心灵天生便已被赋予一种能力,能够区别,在某些行为与情感中,有对的、值得称赞的与美好的性质,而在其他一些行为与情感中,则有错的、应予谴责的与邪恶的性质。
卡德沃斯[71]博士恰当地指出,法律不可能是那些对错区别的根源。因为假定真有这种法律,那么,随之而来的一定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即,或者遵守该法律是对的,而不遵守它是错的,或者我们是否遵守该法律或不遵守它,都无所谓。那种我们是否遵守或不遵守都无所谓的法律,显然不可能是那些对错区别的来源;而且那种遵守是对的而不遵守是错的法律,也不可能是那些对错区别的来源,因为甚至这个遵守它是对的而不遵守它是错的判断,仍须假定有某些对的与错的理念或想法预先存在,并且遵守该法律和那些对的想法同在一边,而不遵守该法律则是和那些错的想法同在另一边。
既然人的心灵在有法律之前便已懂得分辨那些对错,因此,似乎可以推断,心灵必然是从理性得到这种分辨能力的,是理性为心灵指出对错的差别,就像它也为心灵指出真假的差别那样。这个在某些方面虽然是正确的、不过在其他方面却略嫌草率的结论,在抽象的人性科学还只是处在幼稚的发展阶段,而心灵的各种能力究竟有什么不同的作用与功能也还未被仔细考察与分辨清楚之前,比较容易被接受。当与霍布斯先生的争论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人们没想到心灵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能力可以产生任何这种分辨对错的念头。因此,那时候流行的学说,主张美德与邪恶的本质不在于人的行为服从或违背某一上级权威的法律,而在于人的行为服从或违背理性,于是理性就被认为是道德赞许与非难的源头与原理。
美德在于服从理性,就某些方面来说,是正确的,而就某一意义来说,理性也可以很恰当地被看作是赞许与非难以及所有稳健的是非判断的源头与原理。我们正是透过理性,才得以发现我们的行为应该遵守的那些概括性的正义规则。而我们也正是透过同一种机能,才得以对什么是审慎的、什么是端正的、什么是慷慨或高贵的,形成一些比(正义的概念)较模糊和不确定的想法。我们经常怀着这些想法在社会上行走,并且努力尽我们所能,按照这些想法来形塑我们的行为格调。概括性的道德箴言,像所有其他概括性的箴言那样,都是从经验归纳整理得来的。我们从许许多多不同的个别案例中,观察什么使我们的道德机能觉得愉快或不愉快,观察什么是我们的道德机能所赞许的或非难的,然后透过归纳整理这些经验,把那些概括性的规则建立起来。但是,归纳整理始终被认为是理性的一种运作。因此,可以很恰当地说,我们是从理性得到所有那些概括性的行为规则与想法的。然而,我们正是用这些规则与想法来约束我们绝大部分的道德判断的;我们的那些判断,如果完全依靠直接的感觉,肯定会极端地摇摆不定,因为直接的感觉变化无常,不同的健康状态或心情常可使它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于我们的那些最稳健的是非判断服从理性归纳出来的一些箴言与想法的约束,因此,可以很恰当地说,美德的本质在于服从理性,而且就这一点而言,理性也可以被看成是道德赞许与非难的源头与原理。
虽然理性无疑是那些概括性道德规则的源头,而且也是我们依据那些规则所形成的一切道德判断的源头,但是,如果就此推定是非对错的最初感觉源自理性,甚至是在最初赖以形成概括性规则的那些个别的案例经验中,那就全然荒谬与难解了。这些最初的感觉,以及所有其他赖以形成任何概括性规则的实际经验,都不可能是理性的对象,而是直接感觉的对象。我们是透过许多不同的事例发现,某一格调的行为经常按一定的方式使我们觉得愉快,而另一格调的行为则经常使我们觉得不愉快,于是逐渐形成概括性的道德规则的。但是,理性不可能使任何特定的事物直接被我们喜欢或被我们憎恶。理性可以使我们看出,某一事物是获得其他某些自然可喜的或可恶的事物的手段,从而使该事物因其他那些事物的缘故而间接被我们喜欢或被我们憎恶。任何事物,不可能因它本身的缘故而被人喜欢或憎恶,除非被直接的感觉辨别为可喜的或可恶的。因此,如果在每一个别的事例中,美德本身必然使我们觉得愉快,而恶行也同样必然使我们觉得不愉快,那么,如此这般地使我们甘心接受前者并且排斥后者的,就不可能是理性,而是直接的感觉了。
快乐与痛苦分别是我们的喜好与憎恶的主要对象,但是,区分快乐与痛苦的,却不是理性,而是直接的感觉。因此,如果美德本身就是可喜的,而恶行本身也同样就是可恶的,那么,最初区分美德与恶行的,便不可能是理性,而是直接的感觉。
然而,一方面,由于理性在某一意义上可以被恰当地视为道德赞许与非难的原理,另一方面,也由于粗心大意,以致这些赞许与非难的感觉长期被视为根源于理性的运作。哈奇逊博士的功劳在于,他率先相当精密地区分所有道德褒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源自理性,以及它们在什么意义上又可以说基于直接的感觉。在他所举的那些有关道德感的例证中,已经把这一点解释得如此的充分,而且,在我看来,如此的不可反驳,以致关于此一课题如果还有什么争论未了的话,那也只能归咎于人们或者没注意到那位绅士所写的东西,或者对某些措辞方式有一种迷信的执着。后面那个缺点在学术界并非罕见,尤其是在一些像眼前这样深奥有趣的课题上,品格高尚的人甚至往往不愿意放弃任何一句他已习惯视为合宜的成语。
第三节论主张赞许之原理本于感觉的学说
主张感觉是赞许之原理的学说,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别。
(1)某些学者认为,赞许的原理,建立在某一性质独特的感觉上,建立在当心灵遇到某些行为或情感时所发挥的某种特殊的感觉能力上;某些行为或情感使这个特殊的感觉能力发生某种愉快的感动,而其他一些行为或情感则使这个感觉能力发生不愉快的感动,于是前者被盖上对的、值得赞美的与有美德的性质戳记,而后者则被盖上错的、应予谴责的与邪恶的性质戳记。由于这种感动的性质独特,和其他每一种感动的性质不同,并且是某种特殊的感觉能力所产生的效果,所以他们就给它取了一个特殊的名字,称它为一种道德感。
(2)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要说明道德赞许的原理,并不需要假定有任何新的、前所未闻的感觉能力存在。他们认为,自然女神,在这里,就像在所有其他场合那样,采取了最严格节俭的做法,令同一原因产生许多不同的效果。他们认为,同情,这个始终为人所注意,而人心也显然被赋予的能力,足以说明所有被归因于所谓道德感的效果。
哈奇逊博士曾经费心详细地证明赞许的原理不是建立在自爱的基础上。他也曾经证明赞许的原理不可能来自于理性的任何作用。因此,他以为,除了假定自然女神赋予人心某种特殊的能力,再也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产生这种既特殊又重要的效果了。当自爱与理性都被排除了以后,他想不出心灵有什么其他已知的能力似乎还多少合乎这个目的要求。
这种新的感觉能力,他称之为一种道德感,并且认为它有几分类似于外表的感觉器官。正如我们周遭的物体,按一定的方式使那些器官发生感动时,显得具有声音、滋味、气味、颜色等等不同的性质那样,人心的各种不同的感动,按一定的方式触碰这种特殊的能力时,也显得具有可亲的与可厌的、正直的与邪恶的、对的与错的等等不同的性质。
这个学说认为,人心的各种简单的念头或认识全来自于各种不同的感觉或知觉能力,而这些感觉或知觉能力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别,其中一种被称为直接的或先行的感觉能力,而另一种则被称为反射的或后发的感觉能力。[72]直接的感觉能力让人心能够,在没有先行感知到其他任何种类的事物时,对某些种类的事物有所认识或感知。譬如,声音与颜色是某些直接的感觉能力的对象。听到一个声音或看到一种颜色,不需要先行感知到其他任何性质或对象。另一方面,人心透过反射的或后发的感觉能力所感知或认识到的那些种类的事物,需要以先行感知或认识到其他某些种类的事物为其前提。譬如,谐调与美丽是某些反射的感觉能力的对象。要感知到某一段声音的协调或某一种颜色的美丽,我们必须先行感知到那段声音或那种颜色。道德感被认为是一种属于这一类的能力。洛克先生[73]称之为反思并且认为是人心对各种热情与情绪的简单认识赖以形成的那种能力,根据哈奇逊博士的分类,是一种直接的、内在的感觉能力。另外,让我们得以认识那些热情与情绪的美丽或丑陋,认识它们的善良或邪恶的那种能力,根据哈奇逊博士的分类,是一种反射的、内在的感觉能力。
为了进一步支持这个学说,哈奇逊博士还努力证明它合乎自然的类似原理,说人心被赋予其他许多种反射的感觉能力,完全类似道德感,诸如,我们赖以认识对象外表美丑的那种感觉能力;某种所谓对公益的感觉能力,让我们得以和我们的同胞们一起感觉到他们的快乐或痛苦;还有一种对荣辱的感觉能力,以及一种对嘲笑的感觉能力。
但是,尽管这位极富创意的哲学家,为了证明赞许之原理源自某种和外表的感觉器官有几分类似的特殊感觉能力,可以说费尽了心思,然而,却也存在着一些他承认可以从这个学说推衍出来的结果,也许会被许多人认为足以驳倒这个学说。他承认[74],属于任何感觉能力之对象的性质,绝不可以被认为属于该感觉能力本身,否则就太荒谬了。有谁想过要称视觉是黑的或白的,称听觉是响亮的或低沉的,或称味觉是甜美的或苦涩的?因此,在他看来,称我们的道德能力是有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是正直的或邪恶的,也同样荒谬。这些性质属于那些感觉能力的对象,而不属于那些感觉能力本身。因此,如果有什么人的心灵长得是如此的荒谬,以至于把残忍与不义当作最高尚的美德予以赞美,并且把公正与仁慈当作最卑鄙的邪恶予以谴责,则这样的一种心灵构造的确可以被视为对这个人和对社会都是不利的,而且它本身也可以被看成是不可思议的、令人惊奇的与不自然的,但是,它却不可以被称为不道德的或邪恶的。
可是,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看到什么人对着一个残忍的、冤枉的、由某位傲慢自大的暴君下令执行的死刑场面大声鼓掌叫好,我们应该不会认为我们犯了什么严重荒谬的过失,如果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为极端的不道德与邪恶,尽管那种行为只不过表示那个人的道德感觉能力败坏,以致荒谬地把那可恨与可恶的死刑执行场面当作是高贵的、宽宏的与伟大的行为给予赞扬。我想,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旁观者时,我们的心肯定会暂时忘了同情那个受难者,而只感觉到极端厌恶与痛恨这样一个该受天打雷劈的家伙。我们对他的痛恨甚至应该会多于对那个暴君的痛恨,后者可能是受到强烈的忌妒、畏惧和怨恨的心理刺激,因此反而比较可以原谅。相反,旁观者的那种感觉则显得毫无来由或动机,因此,是十足彻底的可恶。我们的内心最难体谅的,最憎恨、气愤与排斥的,莫过于这种颠倒错乱的感觉或情感了;我们非但绝不会认为这种心灵构造只不过是有些奇怪或不妥罢了,说不上有什么不道德或邪恶的性质,反而会认为它是最极致与最可怕的道德堕落阶段。
相反,正确的道德(褒贬)情感,看起来总是多少值得赞美的,总是好德性的。某个人,如果他的赞美与谴责,在所有场合都和他所赞美或谴责的对象的高贵或卑劣极其精确地相配,那么,这个人似乎甚至值得我们给予某一程度的道德赞美。我们钦佩他的道德情感的细致精确:他的那些情感引领我们自己的判断,它们那种非凡的与令人惊奇的公正性,甚至引起我们的惊叹与赞美。没错,我们未必能够确定一个这样的人,在他自己的行为上,也完全和他在品评别人的行为时一样的精确合宜。美德,除了需要有细致精确的情感,还需要有坚定的习惯与决心。有些人徒然有非常精确完美的道德情感,却不幸欠缺坚定的习惯与决心。然而,这种性情,虽然有时候带有一些缺点,却也绝不可能干出什么卑鄙无耻的罪行,并且是那种可以在上面把美德建立起来的最佳基础。有许多人,虽然用心良善,而且也真的打算尽到他们所想到的义务,可是却因为他们的道德情感卑鄙粗暴而令人讨厌。
也许有人会说,虽然赞许的原理不是建立在任何与外表的感官有什么类似的感觉能力上,但它仍然可能建立在某一特殊的感觉上,这种特殊的感觉只合乎这个特定的目的要求,而完全没有其他作用。他们也许会说,赞许与非难是我们在看到各种不同的品行时心中会兴起的某些感觉或情绪;而且正如愤怒或许可以被称为一种受到伤害的感觉,或感激可以被称为一种得到恩惠的感觉,赞许与非难也可以很恰当地被称为一种对错的感觉,或被称为一种道德感。
但是,这种解释,虽然可以避免前述那种反对的意见,却会招来其他一些同样无法辩驳的反对意见。
首先,任何一种特别的情绪,不论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仍然会保有某些一般性的特征,而这些辨别它是属于哪一种情绪的一般性特征,总是比它在不同的个案中所经历的任何变化来得更为醒目与引人注意。譬如,愤怒是某种特别的情绪,因此,它的一般性特征,总是比它在不同的个案中所经历的一切变化更容易辨别。针对某个男人的怒气,无疑稍微有别于针对某个女人的怒气,而后者又稍微有别于针对某个小孩子的怒气。在每一个这样的例子里,一般的怒气因为对象的特性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局部变化,凡是仔细观察的人都很容易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在所有这些例子里,怒气的一般性特征仍然居于显著的地位。要辨识这些一般性特征,不需要怎样细腻的观察能力;相反,要发现它们的局部变化,则必须有敏锐的注意力。每个人都注意到那些一般性特征,却很少有人观察到那些局部性变化。因此,如果赞许与非难的感觉,就像感激与愤怒那样,是一种特别的情绪,和其他每一种情绪明显不同,那我们便该预期,在赞许或非难的感觉可能经历的所有变化中,它仍将保有那些标志它是属于哪一种情绪的一般性特征,而且这些特征一定是清楚明白的、一目了然的、很容易分辨的。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当我们在不同的场合赞许或非难时,如果我们仔细注意我们真正的感觉是什么,那我们将发现我们在某一场合的感觉往往全然不同于在另一个场合的感觉,而且在这些感觉当中根本不可能找到什么共同的特征。譬如,当我们看到一种温柔的、敏锐的与仁慈的情感时,打我们的心底兴起的那种赞许的感觉,便完全不同于我们被一种伟大的、勇敢的与宽宏的情感打动时,心底兴起的那种赞许的感觉。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对那两种情感的赞许也许是十分彻底的,但是,前一种情感使我们的心情变得和蔼,而另一种情感则使我们的心情变得激昂,它们在我们的心中所激起的那些情绪,没有什么相似的性质。但是,根据我一直努力想要建立的那个理论,情形却是必然如此的。由于我们所赞许的那个人的情绪,在那两种场合,彼此是全然相反的,而且也由于我们的赞许源自对那两种相反的情绪的同情,所以,我们在前一种场合所感觉到的,和我们在另一种场合所感觉到的,便不可能有什么相似的性质。但是,如果我们的赞许是一种特殊的情绪,和我们所赞许的那些情感没有什么共同的性质,而是源于我们看到我们所赞许的那些情感,就像我们的其他任何一种热情源于我们看到它的适当对象那样,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发生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非难的场合。我们对残暴冷酷的憎恶,和我们对卑鄙下流的蔑视,没有什么相似的性质。我们在看到那两种不同的恶行时,我们自己心里的感觉,和他们的情感与行为正被我们打量的那些人心里的感觉,固然是不调和的,不过,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不调和。
其次,我已经指出,[75]不仅人心各种被赞许或被非难的热情或情感,在道德上有好坏之分,而且适当与不适当的赞许,对我们自然的感觉来说,也似乎带有同一种好坏之分。因此,我想问,根据这个理论,我们是怎样赞许或非难适当或不适当的赞许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合理的答案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必须说,当我们的邻人对第三人的行为的赞许,和我们自己对那第三人的行为的赞许一致时,我们便会赞许他的赞许;而相反的,当他的赞许和我们自己的感觉不一致时,我们便会非难他的赞许,并且认为他的赞许在道德上多少是不好的。因此,至少在这一个场合,必须承认,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感觉上的一致或对立,构成道德上的赞许或非难。如果在这一个场合事实是这样,那我就要问,为什么在其他每一场合不是这样呢?为什么要设想一种新的感觉能力来解释那些赞许与非难的感觉呢?
对于每一个主张赞许之原理倚赖某种特别的、分明不同于其他每一种感觉的理论,我都将提出下面这个反对的理由: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那上苍无疑要它成为人性的主宰性原理,然而,迄今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以致在任何语言中都没有它的名字,这就很奇怪了。道德感(moralsense)这个名词是最近才形成的,而且迄今也还不能算是正规英语中的一部分。赞许(approbation)这个名词不过是最近这几年才被挪用来特别表示这一类感觉的。就正规的用语来说,凡是让我们觉得完全满足的,我们都可以说我们赞许,譬如,赞许同一栋建筑的形式,赞许一部机器的设计,赞许一盘食物的味道等等。良心(conscience)这个名词并不直接表示任何我们赖以赞许或非难什么的道德能力。没错,良心这个名词假设有某种这样的能力存在,并且恰当地表示我们意识到我们过去的作为符合或违背它的指示。当爱、恨、喜、悲、感激、愤怒,以及其他这么多全被认为臣服于这个主宰性原理的热情,都已经使它们自己重要到足以获得它们的称号时,它们全体的主宰竟然这么不受注意,以致,除了少数几位哲学家,迄今还没有人想到值得给它一个称号,那不是叫人觉得不可思议吗?
当我们赞许任何品行时,我们自己所感觉到的那些情感,根据我在前面尝试建立的理论,来自于四个在某些方面彼此不同的源头。第一,我们对行为人的动机感到同情;第二,我们对因他的行为而受惠的那些人心中的感激感到同情;第三,我们观察到他的品行符合前述那两种同情通常遵守的概括性规则[76];最后,当我们把他的那些行为视为有助于增进个人或社会幸福的行为体系的一部分时,它们好像被这种效用染上了一种美丽的性质,好比任何设计妥善的机器在我们看起来也颇为美丽那样。在任何一个道德褒贬的实例中,扣除了所有必须被承认来自这四个原理的那些道德情感后,我将很乐意知道还有什么情感剩下来,而且我也将爽快地容许这个剩余被归因于某种道德感,或其他任何特殊的能力,只要有人精确地查明这个剩余究竟是什么。如果真有任何这种特殊的原理,或任何像所谓道德感这样特殊的原理存在,那我们或许可以指望在某些特别的实例中感觉到它单独地、个别地、完全和其他任何原理分离地发挥作用,就好像我们时常纯粹地、没有混杂其他任何情绪地感觉到喜悦、悲伤、希望和恐惧那样。然而,我想,根本不可能想象会有那回事。我从未听说这种原理,曾在任何所谓的实例中,能被视为单独地发挥作用,未混杂有同情或反感,未混杂有感激或怨恨,未混杂有关于行为是否和已经确立的规则相符的理解,乃至最后也未混杂有我们对有效用的事物,不论是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一般都会有的那种觉得它们整齐美丽的感觉。
另外有一个理论,也尝试从同情的观点来解释我们的道德情感的起源,它和我一直努力想要建立的那个理论有所不同。这个理论主张美德在于效用,并且以旁观者对效用的受惠者的幸福感到同情,来解释旁观者审视任何品行的效用时所感到的满足与赞许。这种同情,不同于我们对行为人的动机所感到的同情,也不同于我们对因他的行为而受惠的那些人心中的感激所感到的同情。这种同情,和我们赞许一部设计妥善的机器,属于同一种原理。但是,任何机器都不可能是任一种最后提到的那些同情的对象[77]。在本书第4篇,我已经对这个理论稍微作过说明。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
相邻推荐:白鲸 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 春 儒林外史 天幕红尘 时光知味 丑陋的中国人 小学问:解决你的7种人生焦虑 天空的另一半 往事与随想 瓦尔登湖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随园食单 暗箱 教书匠 四世同堂 人猿泰山 故事新编 草:最怀念的某年 笑林广记